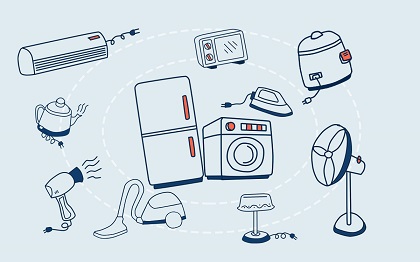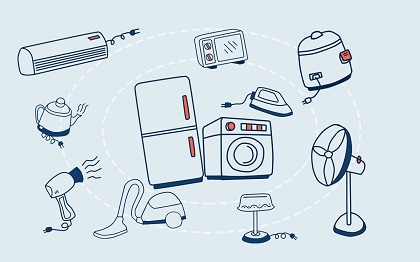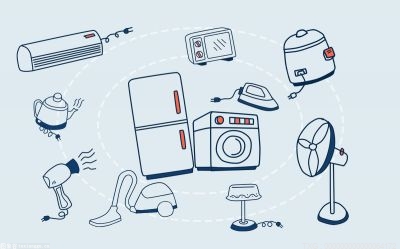◆ 想要成为创造型国家,就应该在国际学术界有自己的特色,要致力于形成“中国学派”
◆ 要从追随模仿,提升到联合起来攻重大问题,在技术上问鼎最前沿,在资源开发上探索新的方向
◆ 当前国民对科普的需求日益高涨,科普已经形成产业,科学家有义务站出来,为打造汉语科普高地作出贡献
文 |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 张建松
地球表面13亿立方千米的水,97%都集中在海洋里。平均水深3700米的海洋,占据了地球表面71%的面积。人类在陆地上繁衍生息,曾把远离自己的海洋留给了神话世界;一旦透过几千米的水深看到了大洋的真面目,回过头来将会更明白自己脚下大陆的真相。
1936年出生的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,致力于推动我国海洋与地球科学发展,提倡强化科学的文化内涵,并身体力行促进海洋科普活动。2018年5月,他以82岁高龄乘坐我国自主研制的“深海勇士”号载人深潜器,在南海三次下潜采样,被誉为真正的“深海勇士”。2021年11月,甘于奉献、勇于探索的汪品先院士当选为“全国道德模范”。近日,本刊记者专访了这位永远保持着对科学热爱的著名海洋地质学家。
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
在学科核心问题上取得原创性突破
《瞭望》: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以来,我国的海洋科技突飞猛进,深海科学研究取得众多成果。你能否谈谈我国的海洋科技现状?
汪品先:我国海洋科技建设确实是突飞猛进。“蛟龙”号、“深海勇士”号、“奋斗者”号载人潜水器和“海斗一号”全海深非载人潜水器接连下水,海底观测网大科学工程、天然气水合物钻采船(大洋钻探船)建造相继启动。“十四五”时期,我国深海探索的深潜、深网、深钻“三深”技术可望齐备,论实力将进入国际领先行列。取得这些成绩非常不易,因为我国的海洋尤其是深海科技的发展起步非常晚。这种高速发展,不仅在国内空前,在国际上也是科技史上的奇迹。
再说科学方面,我国的深海探索从太平洋推进到两极,深入到马里亚纳海沟世界海洋最深处。尤其在南海,通过三十余个单位八年的通力合作,完成了规模空前的“南海深部计划”,为我国在南海赢得了科学上的主导权,使南海正在成为世界边缘海研究的典范。
可以说,我国的海洋事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旺发达,深海科技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全国上下的共同关心。当前我国海洋与地球科学的发展,正处在历史性的黄金时期。现在的任务是要在万马奔腾中保持冷静,在实干的同时也要做好未来规划,才能持续前进。
▲ 2021年8月18日,工作人员在西太平洋准备从“探索一号”科考船甲板布放“奋斗者”号 陈凯姿摄
《瞭望》:此时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?
汪品先:深海探索,自二战后从欧美发展起来,是一部科学和技术携手发展的历史。而作为后发国家,“科”和“技”的融合是我国深海探索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。
缺乏全盘协调,容易出现一拥而上、重复建设的偏向。宏观说来,我国海洋科技的发展正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,需要考虑发展的转型。
不只是海洋科技,整体讲我国科技界的当务之急,都要抓住大好时机,共同促进科学的转型。当前,我国科技队伍规模和SCI论文数量都已经高居世界第一,下一步就是要从量变到质变,从原料输出型转化为深度加工型。
当代的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相似,都在全球化。在经济上,有所谓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国际科技界也有类似的分化:发展中国家科学家主要提供材料、数据,属于原料输出型;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才是将原料加工成型,得出科学结论,属于深度加工型。两者的区别不在文章多少,而是研究类型不同,产生的学术和社会价值更不相同。
这点在包括海洋科学在内的地球科学和宏观生物学领域尤其明显,因为都有很强的地域性。研究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资料,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,数据同样重要。有些自然现象比如说季风,主要就分布在“第三世界”,于是发展中国家也会具有天然的优势。尤其是国土大、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,不但提供“原料”,还可以输出劳务,做劳动密集型的分析工作,因此文章数量不少。但是整体上地球科学的发展趋势,却在向系统科学转化,理论创新的前沿在跨越空间圈层和时间尺度的地球系统科学,从现象描述向机制探索转化。
与传统的地球科学相比,地球系统科学从原始数据到科学解释之间的工序增多,“原料”的加工变深。假如我们仍然满足于输出原料和低加工产品,把深加工、高增值的生产留给别人,若干年后将会发现,我国尽管成为更大的数据输出国,论文数量也许更多,而在学术水平上的国际差距却会拉得更大。
所以说,地球科学也需要转型。我国的出口商品,已经从当年的领带、打火机发展到高铁、手机,我国的科学成果也需要向学科的核心问题进军,需要有原创性的突破,这就是转型。从外国文献里找到题目,买来外国仪器进行分析,然后将取得的结果用外文在国外发表,这当然是我国科学的进步,但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科学上的“外包工”。想要成为创新型国家,就应该在国际学术界有自己的特色,要致力于形成“中国学派”。
警惕“深海陷阱”实现发展战略升级
《瞭望》:你最近说,深海为地球上的生命提供了最大的栖居场所,但是其永恒的黑暗和极端的环境,使得开发者面临巨大的挑战,需要警惕“深海陷阱”。这里的“陷阱”是指什么?
汪品先:指的是深海开发的战略失误和技术失败,原因是人类对深海的了解太不够。海洋200米以下就是永恒的黑暗,我们对深海海底地形的了解还不如火星表面。人类在陆地上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,才发展起农牧业,从采集和渔猎进步到农耕畜牧,学会了利用陆地资源。而深海的开发只有几十年,手段还只是采集和渔猎,还够不上陆地上新石器时代的水平。
首先是不了解深海资源的特点。与陆地不同,深海过程演变往往比陆地慢几个量级:锰结核百万年才长1cm,深部生物圈的繁殖周期以千年计。因此陆地“淘金”式的开发不适用,深海开发有待另辟蹊径。
深海的生物资源,不能仅通过渔业手段从深海索取蛋白质,更要着眼于基因资源。深海生物尤其是微生物有着各种各样的“特殊功能”,有的能适应高温高压,有的有着尺度惊人的长寿能力,提供这些特殊功能的基因就是无价之宝。
深海资源量的估算并不容易,而错误的估算会对深海探索造成误导。1965年,美国专家曾提出太平洋海底有上万亿吨的锰结核可以开采,而且增长的速度比采矿还快。这幅聚宝盆式的图景,诱发了海底采矿的高潮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有上百个航次前往太平洋,70年代以后又纷纷放弃。当时的说法言过其实,深海金属矿的商业开采经济代价太高、环境破坏太大,至今还不容易实现。
另一个重要的教训是根据个别站位的数据,外推到全大洋得出的深海资源量其实并不可靠。比如在深海底下发现的深部生物圈,上世纪90年代根据6个站位推测,全大洋海底下面的微生物占全球活生物量的30%,后来经过大洋钻探核实,从30%降到了0.6%。
再一个“陷阱”就是对技术上的难度估计不足。比如大洋钻探,在上世纪50年代,美国发起时的首要目标就是打穿地壳,采到原位地幔样品;21世纪初日本建成“地球号”大洋钻探船,下水时的口号就是去“打穿地壳”。但是这项目标至今未能实现,其实在地幔的高温高压下进行钻探的技术难点,至今还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。
更为严重的是技术事故。2010年墨西哥湾一个钻井平台创造了钻井纪录,发现了大油田,就在完井结束的当晚由于防喷系统失灵,发生气喷导致钻井平台爆炸沉没,造成11人遇难、17人受伤,喜事变成了丧事。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海底油井漏油,几个月里从1500米深海底涌出了50万立方米原油,造成墨西哥湾北部面积9900平方公里的油污带,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带来了深重灾难,经济损失高达177亿美元。
除此之外,还有战略决策上的失误。比如日本为了预警海上地震与海啸,决定建造深海海底观测网。2003年的计划,是在其东面太平洋俯冲带两侧布网。但是2006年改变主意,改为在日本南边建网。不料,就在南边观测网建成的2011年,9.0级的特大地震发生在日本东边而不是南边。于是又用4年时间,在东边的太平洋俯冲带建起了5700千米长的观测网,规模和投入比原来2003年的计划大得多。
总之,人类对深海“暗世界”的探索刚刚开始,有着无比灿烂的前景,但是需要的是创新而不仅是模仿。当前,我国的深海研究和开发也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,格外需要以史为鉴,研究国际先行国家的经验教训。
《瞭望》:随着我国深海科技实力发展,你认为当前我国深海科技战略需要进一步升级吗?
汪品先:对,应该实现战略升级。这些年,我国深海科技发展主要是以追赶发达国家为目标,缺乏国家层面的整体目标。具体说来,在深海设备上追求技术指标,对应用目的和运行效率不够重视;在科学探索上缺乏顶层设计,研究目标分散化、小型化;在能力建设上过多取决于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,缺乏全盘协调,出现了低水平重复;在国际层面,深海的科技合作尚待进一步加强。
这些前进中的问题,折射出我国海洋科技发展初级阶段的特点。如何及时实现战略升级,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深海探索基本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发展起来的,但走的是一条反复曲折的路。我们需要从中吸取教训,要从追随模仿,提升到联合起来攻关重大问题,在学术上形成特色,在技术上问鼎最前沿,在资源开发上探索新的方向。
为了实现深海科技的战略升级,建议首先要设立“科”“技”结合的国家级深海探索目标。虽然我国目前无论海洋科学还是技术,离国际顶层都还有相当差距,但是已经具备条件,完全可以将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共创新路,结合我国地理条件和科学积累,在国家层面提出共同目标。
其次,要全面协调各方面的积极性,实现错位发展。各地方对发展海洋科技的积极性应当鼓励,同时需要相互协调,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错位发展、各尽所长,避免做“一窝蜂”式的投入。
第三,建议开展我国领衔的国际科学计划。例如在南海可以组织以我为主的深海国际合作计划,无偿吸收南海周边国家科学家参加,必将赢得世界学术界的热烈拥护。再如国际大洋钻探计划,现在美国因资金链脱落暂时退出,我国可以果断出手,争取和欧盟联手共同领衔,并联合原先被排除在深海科技以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,打造深海科技国际合作的新局面。
科学创新要有创新文化的土壤
《瞭望》:2021年,你再次在同济大学开设“科学与文化”公开课。同时还出版了《深海浅说》科普专著,并入驻短视频平台,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关注。你为什么如此重视科学与文化的研究?
汪品先:我做科普,也是从海洋入手的。自上世纪80年代晚期起,我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已有二十多年,年年提交提案、写书面发言呼吁加强海洋意识、制订海洋国策,后来又在各种干部培训班讲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。媒体把这些讲话拿去发表,就成了科普,所以那时候我做科普属于无心插柳。
至于有心栽花做科普,那是近十来年的事,具体说是2013年《十万个为什么(海洋卷)》和2020年的《深海浅说》,都是下了功夫做的。2017年和2021年我在同济大学开设“科学与文化”通识课,对我来说那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科普。
为什么我会把科普看得那么重?
我认为高质量的科普,是科学回归其文化本色的一种途径。科学本来就是文化的一部分,特别是科学创新,必须要有创新文化的土壤;反过来,科学的成果既可以转化为生产力,也可以转化为文化,而我们往往只注意生产力的一面,忽视了文化的一面。我想做的,就是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来推进科学的文化内涵。
高级的科普,也是科学发展本身的要求。科学的突破口,往往是在学科交叉的层面,因此要求科学家尽量用行外人也能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成果,而且科学家本人也只有理解透彻,才能够用简单的语言进行表达。同时,科普也是社会的发展需求。随着社会的进步,当前国民对科普的需求日益高涨,科普已经形成产业,科学家有义务站出来,为打造汉语科普高地作出贡献。
近来我的一些科普短视频在网上受到欢迎,其热烈的程度远远超越了我的预期。隐隐约约我有一种新的感觉,感到和年轻人找到了心灵交往的新平台。再说远一点,这种新平台也有可能正在孕育着一种新的文化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有GDP,还要有软实力。将现代科学和传统文化结合,创造出新一代的中华优秀文化,这正是我们科学家和文化人的共同责任。
刊于《瞭望》2022年第5期
总监制 | 史湘洲
监制 | 杨越